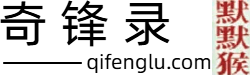补偿之妖刀记番外神玺书第6折:悲智雙運·易地神殊
第6折:悲智雙運·易地神殊
這麼一想,一切便説得通了。
在越浦城外的密林灘岸之上,段慧奴的大隊人馬和勒仙藏都説是循煙花火號而來,勒仙藏更言之鑿鑿地指稱是見從施放,質疑她有誤導之嫌;從時序上説,雖未必全無道理,但見從是徹頭徹尾的自了漢、單幹王,她心裏本沒有“同伴”的概念,遑論刻意隱瞞獄龍一事,私的意圖昭然若揭,在未尋到天龍蜈祖以前,不可能主動叫人來攪局。長孫旭始終覺得有蹊蹺,如今總算真相大白。
放出火號之人,必是最先趕到的勒仙藏。
這位王叔在楊柳岸棋攤安置的眼線,第一時間向他回報騷動,勒仙藏尾隨於天龍蜈祖與箭舟之後,甚至可能追上蜈祖——這也能解釋,為何蜈祖在後段放慢了速度。
奔行間開口説話,真氣一,輕功自是大打折扣;放小舟、見從,乃至段慧奴的人馬進入煉蠱之地,恐怕也非天龍蜈祖的本意,而是出於“國主”的要求,不得不從也。然而,遵從指示的結果,非但丟了獄龍,連心豢養的銅蜈赤蛇也完蛋大吉,天知道獄龍還殺了多少蠱物,此際老魔頭的沖天怒氣,或許是其來有自。
長孫旭只覺懷中嬌軀簌簌顫抖,巧君姑娘此前無論殺人或逃難,都不曾失去沉着,冷靜得令人心寒,而衣櫃內通風有限,兩人身子密貼,兀自升高的體温相互蒸熨,也不可能是因為寒冷。少年不明就裏,仍緊了緊手臂,將玉人摟得更滿,彷彿這樣就能接住她似的。
巧君姑娘一怔回神,輕輕掙動,難得顯出一絲孩子氣似的倔強。九天生是温順的子,不好強人所難,順着她的執拗略松臂圍,仍是貼背環擁,畢竟櫃裏就這麼點地方,外頭天龍蜈祖不消説,連勒仙藏也可能是深藏不的高手,以巧君姑娘玲瓏心竅,當然不會傻到為了鬧彆扭而暴行藏。
蜈祖把話説得忒硬,就算當場翻臉也非不可能,勒仙藏的聲音卻未顯絲毫不滿,聽着依舊和悦平穩,渾無芥蒂。
“師父對我恩同再造,所有人都看我不起的時候,只有您老人家沒有放棄我,莫説坐上國主之位,就算我成了南陵之王,師父永遠都是師父,不會變的。”天龍蜈祖陰陽怪氣地哼了一聲,明顯是十分受用的,聽着已不似前度那般憤烈。
“獄龍固然是我天龍山的至寶,千金萬貴,説到了底,它要能對付見三秋那個老怪物才行,而本門並無成功煉化獄龍的前例。”勒仙藏續道:“要殺見三秋,我為師父準備了兩招殺着,其一是鐵衞軍,其二便是酋首的武功。‘逐世王酋,雙十抱’之名傳遍諸封國,讓這兩頭老虎互相嘶咬,我等作壁上觀即可,連手都不必髒,豈不甚好?”長孫旭頭一回聽到“見三秋”之名,心念略動,登時恍然:“原來‘覺尊’叫見三秋,他的徒弟一個叫見從,另一個叫柳見殘,全是見字輩,興許是門派裏的規矩。”而“逐世王酋”韋無出的名號,則連遠在東海的少年都如雷貫耳。
此人極之神秘,如神龍見首不見尾,最著名的事蹟就是格斃諸鳳殿遊俠之首李桑,以及一手訓練出悍猛絕倫的赤尖山飛虎寨“十五飛虎”,在南陵諸國間橫行無忌,為禍劇烈。奇怪的是:韋無出鎖定的劫掠對象,絕大部分都是當時的鎮南將軍段思宗的敵人,或為暗裏反抗央土朝廷的勢力,或為拒絕加入南陵聯盟的國家,一度被認為與南鎮有所勾結,甚至是段思宗本人所扮。
然而,靠着一枝健筆以及非凡的膽識謀略,由一介南疆荒僻小縣的縣令,一躍成為堂堂南鎮,藉由捭闔縱橫之術,將諸封國團結在鎮南將軍府的軍旗之下,完成我朝順慶皇帝數十萬南征大軍都沒能達成的目標,將南陵諸封國實質納於央土朝廷的轄權內……辦到了數百年來無人能及之功業的段思宗,在南陵諸國間擁有極高的威望,他是以英雄魄力和同理土人、不以上國自居的智慧贏得尊敬;南人一向崇拜英雄,把韋無出這種惡寇與“代巡大人”——這是他們對段思宗的敬稱——相提並論,嚴重冒犯了他們對英雄豪傑的敬意。
但在央土的京師平望,對這個謠言的理解就完全不同了,乃至順慶皇帝后來將段思宗召回京師,隨便找了個藉口軟在御賜的華邸美園時,還有人認為陛下太惜情,對這種狼子野心之輩就該拿出鐵腕魄力,夷他九族才是。
當然,這也不純是間關萬里、風土殊異所造成的兩極説法,段思宗回京述職、忽遭軟之後,韋無出這人就像化為煙塵也似,突然便不見了蹤影,以致赤尖山上羣寇無首,最終被孤竹、嶧陽等諸國聯軍剿滅,威懾南陵一時的“十五飛虎”自此除名,只餘罄竹書惡,以儆世人。
巧君姑娘是段慧奴的貼身侍女,對這些事的瞭解在他之上,對“逐世王酋”此一匪號的反應果然很大,長孫旭可以清楚覺到女郎嬌軀繃緊,還沁着細汗的雪潤腮幫驀地繃出稜峭線條,還好沒迸出咬牙的格格輕響,顯然已是極力剋制。
天龍蜈祖鴟鴞般的一聲怪哼。
“瞧你這話説的,若被韋無出那廝聽見,還想要命不?”勒仙藏笑道:“我倆師徒一體,徒兒不怕。況且酋首屬意我上位,也非念着人情義理,而是看中我對那‘螭虎印’略有研究,能助他成事,師父卻不同。當年在我和勒雲高之間,師父您老人家可是選了我的。”天龍蜈祖冷笑道:“勒雲高那白眼狼嫌我天龍山的玩意污穢,頗有貶抑之意,誰知打不過長孫天宗,才巴巴的跑回來找我,當我天龍山是娼寮寨,有錢便能瞎逛麼?本想讓他把段思宗的寶貝女兒活活成蟲,引來鎮南將軍的報復,才特意給了他‘女陰獄’的;豈料這活寶捨不得千嬌百媚的,只肯她眼,還囑咐側近保守秘密,不得向主母漏媾其實該的是腿心裏的兒,非是後拉屎的地方。”猥的笑聲嘶嘎刺耳,聽得人雞皮聳立,腳心刺癢難當。
這人莫不會連聲音都能放毒——正這麼想着,女郎忽揪緊了九的手掌,如溺水者攀住浮木,酥滑柔膩的小小掌心裏濕滑一片,居然全是冷汗。
少年立時會過意來:“連她侍奉的段慧奴都被人矇蔽,巧君姑娘誤把菊當作媾合所入,也是理所當然。”娘娘每月來紅總有幾天不便,由侍女代受針砭,那是天經地義。為免被子窺出蹊蹺,料想勒雲高不好明着走另一處,只能享用後庭,將錯就錯,造就了這一批旱道嫺於男女情事的童貞侍女,和段慧奴一般模樣。
長孫旭本以為説服她尚需若干口舌,好在始作俑者自陳其罪,倒省了他不少氣力,誰知巧君姑娘是個劍及履及的子,沒等天井內正説着話的兩人離去,小手往他腿間一撈。
少年猝不及防,只能苦苦抑住聲息,儘量順着女郎的動作隨她擺,以免發出聲響,引來敵人。
長孫旭雖才剛失了童子之身,在風月冊方面可説是博覽羣書的大家,實作不夠理論來湊。
但他還沒想好該去哪裏。
东海道民生富庶,行的佛教风尚都是些混杂了本地龙王大明神信仰的什锦杂烩,并无殷实的佛法底蕴,沦為富户豪门炫耀财富的肤浅门路,寺庙无不是金碧辉煌,宏伟气派。这座阁子绝不算小,然而远远不是主祀大殿的规模,连偏院都称不上,充其量也就是个放大了的佛堂,阁中地面遍铺大片的青石地砖,打磨光滑,其上的渐层云纹氤氲转,一看就知道是上等货。
雕成莲座模样的三阶神坛作长方形,宽度足有两丈餘,十分气派。相较於此,坛上那尊约一人多高、贴满金箔的佛像就略显单薄,只是它奇特的造型仍是攫取了少年的注目:那“佛像”乃盘翘起一条腿的立像,头戴莲冠,兽面僚牙,模样十分狰狞;背后生了十几对细小手臂,多到长孙旭来不及数,而最接近正常人比例和位置的一双主臂间,则环抱着一隻小得多的赤玉像,略显夸张的凹凸曲线一见便知是女子,两条姣美的腿儿盘在男神际,姿态十分诱人。
不仅如此,玉像半转过一张闭目张嘴的緻小脸,彷彿凝自构的高瞬间,雕得维妙维肖,居然与巧君姑娘有几分相似。
不僅如此,閣內兩側迴廊似的美雕欄,長孫旭判斷是擺放五百羅漢或卅三天人一類複數神像的立龕,此際也已悉數撤去,掛上簾幔,肯定是因應南陵人的小乘信仰,才刻意改變了原有的佈置。
“歡喜佛……不是南陵信仰,這是外道。”巧君姑娘勉力凝眸,瞧了一眼,翹的瓊鼻中輕輕一哼,甚至蔑冷。
“‘歡喜天’乃是象頭雙身,雕作靠背挽手的形象,非是如此;而明王、明妃作環抱合貌,是象徵慈慧同修,又稱之為‘悲智雙運’,豈有着意刻劃私處的道理?出這種無聊玩意之人,既無意、也不懂小乘佛學,只有滿滿的狂悖傲慢,自以為是。”那就不是段慧奴指定的了,少年心想。她從小在南陵長成,更掌嶧陽國大權逾十年,在諸封國的盟會里捭闔縱橫,不會不懂這些細膩枝節。
“是勒仙藏麼?”但出口又覺無稽。除非嶧陽不信小乘,不然那廝可是土生土長的南陵人,沒吃過豬也看過豬走路,整這出也太沒必要。
果然巧君姑娘昏沉地搖搖腦袋,停了一停,才輕聲道:“不是他。”瞥見神壇之下橫置一物,似覆草蓆又未全蓋,隨口問道:“那是……那是什麼?”其實長孫旭一進來就瞧見了,若女郎未曾問起,他是沒打算説的,這下子避無可避,訥訥道:“是何嬤的屍體。”言又止,生生忍住了一聲嘆息。
女郎微微蹙眉:“你怎知是——”省起覆蓋屍體的草蓆何以並未全遮,刻意出何嬤的頭面,奮力瞠開波光滴的濛星眸,揪緊少年的衣布低道:“不好,是陷阱!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