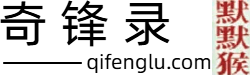补偿之妖刀记番外神玺书第5折:香尘径·女狱阴如
第5折:香尘径·女狱阴如
长孙旭心知“香尘贰”房只能暂避,何吗想方设法把人骗进偏间,与她勾结之人就算不是躲在里头,也必从偏间的密道中进出,说不定何吗原本只是想去把暗门打开,恰遇女郎在此,才巧言赚她进去。
香尘贰的禪房内只有那座乌木衣柜可躲,上头却掛着长年未开之锁,可见常负责洒扫的沙弥有多马虎敷衍。
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掩护。
“没钥匙打不开锁”——这麼想是理所当然的,更何况这枚铜锁异常结实,更能加深这个印象。长孙旭暗自祈求柜中不要有杂物,运起神璽圣功,将锁閂穿过的两枚合叶连着铜锁扭了下来。女郎到这会儿才微诧,似乎明白了他的目的。
锁头是打不开的,但只要能取下合叶,锁就没用了。
长孙旭是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心态一试,没想到神璽圣功配上新得的《不败帝心》,竟有如斯威力。果然衣柜内空空如也,连一件能蔽体的旧僧袍也无,所幸亦无积尘,躲进去不致猛打喷嚏。
他明白下一步才是关键,绝对不能失败,尽起圣功,集中於双手拇指,将两扇柜门连着合叶基座的寸许处,硬生生刮出三两分深的浅槽,堪堪进合叶掛锁,闭起柜门时能牢牢嵌住。
两人躲入衣柜,长孙旭从里头扣着柜门与合叶掛锁,闭起并调整到定位,然后像捏黏土似的将合叶末端反折压进柜门里,然后祈祷从外头看不出什麼破绽。
乌木柜做得浑无罅隙,两人关在里头只怕要闷死,少年灵机一动,食指在柜顶戳出几个可供呼的圆孔,顺便借光;微光中见得女郎睇来一双妙目,訥訥挠头:“我……我天生力气大些,胖子嘛。”女郎的嘴角似微扬,又硬生生抑住,但只这片刻间的似笑非笑,原本的文静端庄里又多几分冷鋭犀利,美到令他无法对视,回过神才听见自己说:“姐姐……怎麼称呼?”呵呵,烂死了。这种时候你问人家的名字做什麼!他直想抱头蹲下,狠狠地撞柜门几记。
女郎“噗赤”一声笑出来,举手掩口,美眄转,真是比仙女还仙。
长孙旭都看傻了,被她直勾勾的目光盯得低下头,女郎似习惯与人对视,而且绝不转开,眸光若能当实剑使,这名秀丽女子的杀伤力恐不在见从之下。
“我叫巧君。”她轻声道。
“我爹总爱这般喊我。”她说的其实是实话。父亲学富五车,亦通卜算,替她排了命盘,发现女儿之命贵不可言,既有后相,复兆将星,是捭闔纵横、动輒天下惊的格局,举世罕有,相书上说若不以贱名呼之,必定夭折。他当趣闻笑话来讲,据说把嚷亲都吓哭了。
习字时,父亲教了她两个名字,圈起“巧君”二字,怡然笑道:“你原本该叫这个名儿的,是娘怕你长不大,教爹莫与命数斗,非给你个平安保全的闺名不可。你让人叫另一个名字不妨,要记住爹对你的期望,巧慧未必是福,只与诗书為奴;心气之所至,亦是女君子。”少年不知她心中所想,傻笑着抓头。
“我……我叫九,巧、巧……巧……那个……巧……”涨红了脸,半天都喊不出口。这就是女郎最不欣赏的那种情,有人可能觉得靦腆的样子很可爱,但她只觉烦躁而已,死去的父亲或死去的丈夫,都不是这种拖泥带水的温子。
男人——或说英雄——最重要的价值,是心气。
心气若高,文人亦可铁马金戈,气万里如虎。而温掩捂久了,若不能有所长进,最后就会变成洗焕云那种猥琐黯淡,如腐般的存在,连英俊的外貌也不能稍掩。
从何吗提起湖衣开始,她便察觉有异,直觉妇人是想让自己进入偏间密道。长云寺的基地是洗焕云一手建立,密道也是他亲自向她报告,近侍之中只有何吗一同与闻;若有人想利用密道搞事,洗焕云肯定不了嫌疑。
他还握有调动兵马的大权,深夜撤哨、製造防御漏,乃至授意西北铁卫军袭杀值勤的丹心灰卫士……这是隻有洗焕云才能执行的阴谋。
何吗从幼年便跟随她的双亲,是南镇幕宾一系的旧人,忠诚度无可挑剔,就跟洗焕云一样,但这本身就是盲点。与洗焕云面谈之后,女郎彻夜难眠,才会在清晨悄悄起身冲凉,想略抑烦躁之,就是突然觉得:此番北上似是选错了人,让洗焕云执掌兵符是个失误,他的无能与心不在焉,恐怕会使一行人陷入危机。
吴先生不只一次暗示她要处理洗焕云的婚姻大事,按这位老西席的意思,挑个貌美柔顺的嶧阳贵女联姻是最好,公私两利,既能加强女郎嫡系的南镇幕宾派与本地贵女的关系,焕云成亲后也能更成稳重,没有其他无用心思。
至於放形骸、非常适应南陵贵族乱风气的舟楚客,反而从不关心女郎跟谁睡觉,别搞出小孩就行。她一直觉得如果开口徵询舟楚客的意见,他定会说出令自己呕血三升、又气又好笑的荒谬歪理,如“你就陪洗家小子睡嘛,睡过就觉没意思了”之类。
但他们都不曾质疑过洗鋭宾之子的忠诚。
“巧……巧……”回神长孙旭还在结巴,女郎谨慎剋制着不耐,轻声引导他。
“巧君。”
“巧……巧君姑……姑……”天啊。她决定径入正题。
“怎麼?”
“人……人来了。”果然跳过名儿他就正常了。少年的冷静机她并不讨厌。
“我听见了声息。他们定会入房搜索,就算打不开柜门,也会试图入刀尖,所以我们得避到那儿。”指着靠墙的一侧。这衣柜虽大,但两人若是全挤到一边,势必得紧贴身子,女郎近乎全,他大概以為她会非常抗拒,打算绕着圈子解释一二。这点将就与命相比,哪有什麼好考虑的?
“无妨。”她忍住嗤之以鼻的衝动,大方倚着壁里一侧的衣柜板,淡道:“你过来罢。”见他面红耳赤,眼睛不知该往哪儿摆,省起自己披着袍子,背门还算有点遮掩,正面却是完全赤的,北人讲礼仪诗书,在这种地方就是扭捏得紧,径调了个头,面朝柜板道:“行了,快过来!”长孙旭才靠过来。
兩人上身背相貼,勉強擠到一側,但九的下半身卻離得她大老遠的,女郎眼角餘光都瞥見他的股翹過門隙,瞧着同番鴨差不了多少,差點沒忍住笑,蹙眉道:“你股是刀槍不入麼?少時若被刺出血來,豈能瞞過?快點過來!”這道理長孫旭也很清楚,聽見偏間暗門被破的聲音,眼看沒法拖了,絕望地把下身一靠,
今是到嶧陽鐵衞軍的大本營,才痛痛快快洗了個噴香舒適的澡,不想卻是危機前的最後一樂。
“對不起對不起對不起……”他小聲地拼命道歉。
“……噤聲!”女郎咬牙輕斥,充滿威儀的短句甚至毋須惡聲,他就像聽見命令似的本能閉嘴。有趣的是:理上長孫旭知道她並不是先前所想像的那種柔弱如水的温婉女子,光是從容身體又無一絲冶放蕩、甚至不讓人生出輕視之心這點,就不是普通女子能辦到。
但他仍覺得巧君姑娘很有氣質,絕對是被段慧奴脅迫來當侍女的南陵某公主,才得有這般泱泱無倫的優雅和氣度。
扮作黑衣夜行模樣的鐵衞軍果然逐間搜索,“香塵貳”也不例外,那小組長以刀柄敲擊銅鎖時,長孫旭徑於櫃門內捏住合葉,自然絲紋不動,刀板入門縫也在預料之中,但二人仍遲未出門回報。
長孫旭轉念一想,暗叫不好:“糟糕,他們在聽呼心跳!”身負神璽聖功的少年呼悠長,心搏可控制到幾難察覺的程度,但巧君姑娘身無武功,無法逃過舞者的耳目探查,而她恰好也想到了這一點,回過頭來,蹙眉出“糟糕”的神情。
越想抑制心跳,它就跳得越快。呼也是。
女郎臉泛桃紅,巧額沁出薄汗,咚咚咚的心跳撞擊着腔,瞧着像要不過氣來。長孫旭福至心靈,一把銜住她微噘的櫻,緩緩度入氣息;雙掌由她滑膩的脅腋下穿出,滿滿握住軟滑彈手的玲瓏玉,掌底口中雙管齊下,神璽聖功純緻密的真氣瞬間滲透嬌軀,如水融般,連結起兩人的經脈氣血,迅速趨於一致。
少年如遁入虛境,心無雜念,而至物我兩忘,與他渾成一體的女郎亦若是。
長孫旭若能再受那位異人仔細點撥,於內功一門究其道理,當知有更便捷有效的傳功法門,這種如水壓滲透的同步法極耗真力,若非聖功、帝心與獄龍函漿三者合一,等閒承受不了這樣不設門檻的劇烈耗損。
即使如此,長孫旭也只能拖到黑衣人出門回報,鬆開嘴巴,貼着巧君姑娘柔的面頰氣着。
女郎額髮輕抵櫃板,吁吁嬌不止,長孫旭雖然愛出“送耿照去嫖”之類的鬼主意,事實上他連女孩子的手都沒牽過,迄今仍是童男,同女子往來實在太費勁了,不合他“省柴慢火”的座右銘。他應該要張皇失措地鬆開魔爪,向巧君姑娘賠罪。
巧君姑娘稍稍撐直了藕臂,翹起的綿股緊壓着的小九,像是伸了個謹慎的懶也似,拘謹地藏起那份舒。少年收緊了指縫,女郎的息聲像被撥動絲絃的樂器一般,忠實反映着彈奏嬌軀的結果。
“舒服……”他聽見她輕哼着,這聲音竟比他想像中更酥更軟,更有女人味,卻非故作柔魅惑撒嬌,而是原本的冷冽中被充分進了慾望,不作偽的誠實反而更加誘人。
房外的天井之中,鐵衞軍拖來被俘虜的侍女,由外側攻堅的首腦回報,可知與二人的料想相去不遠,冼煥雲趁吳卿才帶走了一半的丹心灰衞士,乘夜對剩下的守衞發動奇襲,從密道殺回的正是原本駐紮於小乘僧團處的鐵衞軍。
出人意料的是:就連丹心灰之中,也有冼煥雲的人馬,被撤去的制高點崗哨其實就是回頭來殺同僚的,與爬上閣樓眺望的長孫旭不過前腳走後腳放之差。實際被殺的衞士不過二十來人,其他全是窩裏反的叛賊。
冼煥雲厲聲問段慧奴的下落,眾侍女被姦時雖哭叫極慘,這會兒倒沒個説話的,連原本的噎啜泣聲都一靜,頗有視死如歸的壯烈之。長孫旭暗忖:“説不定她們和巧君姑娘一樣,全是宗室貴女,可惜全得死在這裏。”知苦刑之下沒有好漢,只是在吐實前,不知要受多少折磨,於心不忍,恨不得摀住耳朵不聽。
卻聽一把腔調詭異的嘶嘎嗓音怪笑道:“別殺了,都留着,一會兒問什麼她們都會乖乖招供。統軍大人聽過那……沒有?”中間迸出一串刺耳鳥語,約莫是南陵土話,竟是天龍蜈祖。
鐵衞軍背叛段慧奴,率兵的冼煥雲卻與天龍山的餘孽勾結……道理上雖然不是説不通,畢竟敵人的敵人就是朋友,但長孫旭總覺其中詭秘重重,有着説不出的雲遮霧沼。
冼煥雲冷哼道:“本鎮乃堂堂武人,不涉陰小道,蜈祖所言,未曾聽聞。”
“……央土話該翻作‘女陰獄’罷?”天龍蜈祖似是不以為意,嘎嘎笑道:“這種蠱蟲只能存活於女子合處,平生最怕陽,灌入足夠多的水,便能壓制其生長。本門先人養這‘女陰獄’,本是為了練功之用,以秘法將蠱煉至陽物之上,與染蠱女子合,功力突飛猛進,練一年抵常人三五年;但不幸散功的話蠱蟲便即孵化,死得慘不堪言。”
“這等噁心言語,就不必再説了。”冼煥雲的聲音裏有明顯的嫌惡:“用毒與用刑,一般的是供,不勞蜈祖費心。來人,把她給我架起來!”也不知是挑了哪個可憐侍女殺雞儆猴。
卻聽蜈祖笑道:“本座昨晚,已在食水中放了‘女陰獄’,你們全中了毒。先不説需要陽才能抑制蠱蟲孵化,光是此蠱刺女子情慾的副作用,便能生生熬死了你們,哪個先説出段慧奴躲在哪兒,本座就賞她這大兒,煞煞癢!”長孫旭想到他那癩蛤蟆似的醜樣,幾反胃,搞不懂這個威脅的意義在哪裏。這幫侍女已遭鐵衞軍蹂躪過一輪,要找男人也輪不到這醜陋噁心的老頭,不僅對她們毫無説服力,冼煥雲更不可能理會。
驀聽前院裏一陣喊叫,人馬雜沓,一名鐵衞軍倉皇飛報:“不好了,不好了!啓……啓稟統軍,弟兄們像是中了毒,模樣……模樣很是奇怪……”冼煥雲厲聲道:“慌什麼!天龍蜈祖,你對我麾下的軍士做了什麼!”跟着一陣清脆的拔刀聲響,可以想見眾人將蜈祖團團包圍的場面。
天龍蜈祖怪笑:“本座的‘女陰獄’是改良過的,男子的瞬間,防護不了自身,一樣會中毒。我勸你將那些人燒掉,以免傳染給其他人,不過在燒死之前,可讓這幫丫頭瞧瞧,立刻便老實了。”説話之間,外頭的騷亂急速惡化,不知是死了更多強暴侍女的鐵衞軍士兵,還是中毒之人的模樣太過嚇人。
冼煥雲急着壓制場面,命眾人帶了俘虜往外去,不多時傳來侍女們幾近崩潰的尖叫,使蜈祖之言更增説服力。
天井中似已無人,吵嚷都在前院裏,寺中全是鐵衞軍,眼下就算出了衣櫃也無法逃離,不如待在櫃裏安全。
長孫旭發現巧君姑娘渾身顫抖,無論是掌中握着的堅玉,全都滾燙得不得了,料想她也中了“女陰獄”的蠱毒,受其動情的副作用所影響,故雙被握時才未明顯抗拒,反而小聲説了“舒服”。
他正想出言安幾句,女郎卻反手握住。
兩人貼背而立後,長孫旭才發現女郎還比自已高着一些,其窈窕曼妙不是説着玩的,較男兒明顯為高,單論腿腳,還長了他大半截;踮起修長的腳掌,居高臨下地輕搖抵坐,長孫旭簡直無處可逃,雙掌從玉移到她上,像是要阻止但全沒作用地虛抱着,女郎的股如肢一樣薄,卻無一絲稜峭骨,全是充滿彈的緊實肌,與文靜秀氣的外表毫不相稱。
而她那雙長腿也是。細直的大腿沒比長孫旭的胳膊上多少,長而秀氣的足脛甚至比他的手腕更細,仙鶴化成的天女大概也就是這樣了,緊緻卻不過分發達的肌束瞧着十分有力,一踮腳便繃起姣美的線條,光瞧一眼長孫旭就想了。
這雙結實的美腿,實在……實在太了!
不是搔首姿的,而是:她鍛鍊得恰到好處。
巧君姑娘的細動起來像蛇一樣,連韻律有致的輕緩都温婉可人,好看得不得了,比她截話或命令他時更近於“仙子”的形象,偏偏是做着這麼羞人的事,對心臟的爆擊非常非常地不健康,有直接縮短生命的效果。
少年這才意識到,自己的是玉人的小巧菊。
女郎小臉酡紅,媚眼如絲,劇烈地着氣,可能是高未褪,更有可能是“女陰獄”蠱本未解,她等於全程都被媚藥熬着,不出事情才奇怪。
正想好好解釋,巧君姑娘卻突然捧起他的臉,呵出芝蘭般的濕熱香息,微眯着水波盈盈的酥茫星眸,喃喃道:“我是不能死的,很難讓你明白。用你解蠱毒非我原意,但這樣對我們是最好的。”長孫旭多少有點心理準備,聽得她直言無隱,失落卻較想像中更強,比巧君姑娘不是未經人事的守貞處子更讓人難受。但被藥到進錯兒也太好笑了,少年強打起神,温言道:“巧君姑娘,方才那樣……是解不了毒的,咱們進錯門了。”女郎俏臉微沉。這少年肯定猾頭,否則豈能逃過見從的狙殺?誰知死到臨頭,還來説這些渾話!可能是餘毒的影響,她有些剋制不住,罕見地反口道:“你對男女情事一無所知,胡説八道什麼?媾也只能是這一處,自有天地以來便是如此。前頭……前頭是的地方,便如男子的馬眼,那是用刑之處,還是你竟讓人馬眼麼?”長孫旭目瞪口呆。她説得絕對是錯的,但例證周延,他居然無法反駁。
等、等一下!
“媾只能是這處”説的是菊的話,那麼巧君姑娘的……莫非她還是……
段慧奴覺得被少年瞧扁了,頓有些無名火起,對他的歉疚也就消淡了些。
長孫旭是一定得死的,為徹底掌握窮山一國,這條方略多年前便已定下,眾人努力至今,好不容易才到了收穫成果的時候,不能因為婦人之仁,而影響了統合南陵的大計。
勒雲高死後,她便拋棄了身為女人的部分,貞對她來説其實可有可無,就算她順從南陵貴族的風尚縱情享樂,也不會遭致批評,她只是沒有心思在這裏。把這個只有丈夫享用過的銷魂給他,換少年的命以解“女陰獄”,是女郎所能做到的最後慈悲。
她見過死於“女陰獄”的恐怖屍體,哪怕那曾是她深深愛過的男人,她也沒法再看第二眼。如果不能解去蠱毒,堅強剛毅如段慧奴,怕也只能選擇結束自己的生命。
勒雲高教會了懵懂無知的少女媾的樂趣。嫁給他之後,段慧奴養成了每晚飲蜂水、用花果香油清潔腸道的習慣,期待着她的男人填滿、刨颳着她;雖然沒能得到子嗣至為遺憾,然而她從不後悔遠嫁嶧陽。
這個狡猾的頭小子,居然想騙她走旱道!女郎盯着他瞠目結舌的傻臉,心中冷笑,但適才他那過人的硬碩大,似乎還留在腔壁的深處,小股裏又疼又麻,舒服得不得了,油潤腸忽然湧出,實還想再來一次——“天龍蜈祖!”冼煥雲的聲音倏忽而至,兩人都嚇了一跳,抱着不敢妄動。驀聽統軍使暴怒道:“你把人都死了,我等上哪兒找段慧奴去?萬一覺尊的徒弟識破調虎離山,返回此間,是你要負責應付麼?”天龍蜈祖道:“你鐵衞軍有幾百號人,怕了區區兩名刀客,難怪段慧奴瞧你不起,不讓你。”這話正踩着冼煥雲的痛腳,鏗啷一響利刃出鞘,統軍使森然怒道:“蜈祖是想試試鐵衞軍幾百號人,能再滅你天龍山一次麼?”老人的怪笑如鴟鴞,聽得出滿滿的憤恨怒火,惡鬥一觸即發。
忽聽一人怡然笑道:“兩位都是我嶧陽國的股肱之臣,便不看小王之面,也莫忘了酋首慨然襄助我等,期望殷切,是不是在大敵未滅前,先放一放過往嫌隙?”聲音雖是極,口吻卻陌生,似乎換個説話的方式,少年便能想起近期在哪兒聽過或見過這人。
冼煥雲還刀入鞘,恭謹問候:“參見主公。”天龍蜈祖冷哼一聲,卻未説話。
那人笑道:“煥雲,這是天龍山的化骨散,無論死活,染蠱之人焚燒以前,都先灑上再點火,可止傳染。還能動的切莫靠近,以弓箭個幾輪,可徐徐圖之。”冼煥雲領命而去。
天井中安靜了一會兒,那人才道:“師父您老人家先別生氣,獄龍我已派人去尋,有機會找回來的。只是‘女陰獄’忒厲害的毒物,暫時還是別用啦,以免增加不必要的麻煩。”天龍蜈祖冷笑道:“國主這聲‘師父’,本座可擔待不起。有了強力的靠山,天龍山就不是玩意了,這種過河拆橋的壞習慣得改。這‘女陰獄’不過是想提醒國主,不要步上你老哥勒雲高的後塵。”長孫旭這才會過意來,不頭皮發麻。
原來是那沒用的廢物王叔——勒仙藏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