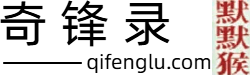补偿免费小说之妖刀记番外神玺书第1折:耿照好友日久的故事
第1折:友同合璧·窍似连珠
长孙旭漫步在兴寧寺外的水渠边。
夜风扑面,掺杂了河水、木舟,乃至食的香气;远处象徵子时的梆响,与擦肩而过的熙攘人声呼应着。四处垂掛的大红灯笼之上,浮挹着晕霞靄,虽是金灿灿的夺人眼目,却也凸显出烛照未及处的夜沉,可说既幻又现实,无论意识到哪一面都令人战慄不已。
越浦是座不夜城。
即使城主独孤天威是浮夸张扬的子,影城一年到头,也只元宵那几天能有这般光景,岂料越浦城内夜夜皆然,委实令人咋舌。
据说在镇东将军慕容柔走马上任之前,越浦的夜晚热闹十倍不止,鬼市的规模远非如今可比。
不让老越浦在集子里酒足饭饱、掏耳洗脚了才回家睡觉,仇深堪比弒父杀母,无怪乎一提到这位贼狠的慕容将军,时人多以“酷吏”呼之,就没句好言语。
九——这是长孙旭在影城同儕之间的绰号,乍看是以“旭”字拆成,据说在南方土话音近“了狗”,总不是什麼好话——自小在北地长成,初到朱城山下的王化镇已觉无比繁华,此番前来,才知什麼叫目光如豆,自己还真是没见过世面的乡下人。
影城一行抵达越浦不久,二总管就被召进阿兰山的栖凤馆了,仅贴身丫鬟霽儿随行,手下均驻扎於兴寧寺的吉光院。以独孤天威一等昭信侯的身份,不仅栖凤馆留有他的居所,连越浦亦有专责招待昭信侯的驛馆,独孤天威带了亲卫、姬人等三百餘名,把驛馆所在的整个街航全包了,镇与城尹梁子同等饮酒作乐,懒上阿兰山掺和。
横疏影从执敬司中挑选十数名亲信,连同使唤惯了的僕妇下人等,也不过三十人上下,安排住进吉光院里,免教独孤天威閒来没事,净找手下麻烦。
“……我等你到丑时一刻。”九完成今的工作溜出吉光院时,统率执敬司的钟阳不知从哪儿冒出来,在他背后冷道:“误了时辰,明儿别想再出门。”九本来想说“不是应该先派两个人看住我”之类,转念又觉钟阳殊不容易,何必刺个对自己尚称宽容的人?举起白胖手掌挥了挥,头也没回,灰溜溜自后门钻了出去,以胖子来说身手算是相当俐落。
钟阳是执敬司的门面,是最符合人们对“二总管亲信”的印象之人:高大、明,气宇轩昂,出身良好,将来便不做昭信侯的股肱之臣,在外也能功成名就,光看外表就知道是天之骄子,潜力十足的新秀。
当所有执敬司的老人对二总管拔擢耿照和长孙旭,表现出强烈的反弹不解,钟阳的泰然自若,也就格外显得与眾不同。
那个山下铁匠的儿子到底有甚价值,钟阳本无法、也无意理解,但九对二总管的意义倒是再清楚也不过——这小胖子一人能顶三位账房先生,还只需要原本一半不到的时间,横疏影就该把他养在笼子里吃好喝好,除了拨算盘啥也别干。
九算数甚至还用不着算盘。
得到这个强大的运算头脑后,二总管喜不自胜,构思起一套全新的经营手法,在年头便把整年要花的钱先算出来,然后推估收益,进行调整,藉此规避风险、补短截长,以谋求更大的商业收益……
儘管横疏影说得眉飞舞,钟阳却完全听不懂,但早在启程往越浦的一个多月前,二总管便挪出人手把钱粮书册转成复杂的暗码,整理出十来箱的文档,专车押运,便於长孙旭在旅途中继续那个难懂的伟大构想。
钟阳甚至觉得,就连转译所用的那套符码号记,都是出自长孙旭之手。
这小胖子拿着那叠天书也似的鬼画符随意翻看,毋须对照号记,就能工作,每天都能总结几页鬼画符文字,由钟阳封入蜡丸锦盒,命人专程送入栖凤馆——二总管手边那份破译的参照图表,还是钟阳亲手抄录的。所有经手的人里,只有长孙旭不需要参照图,彷彿脑中有份现成的,还能同步转换,毫无困难。
肯定是他。钟阳几能如此断定。
二总管赴阿兰山之前,嘱咐钟阳好生照管他,口气虽是轻描淡写,以少年追随她多年的经验,明白长孙旭对二总管的重要,这份託可说是重中之重,不容有失。
长孙旭独居一座小院,饮食皆由专人送入,在里头干什麼谁也管不着,反正天一亮钟阳便会去收缴前的工作成果。餘人虽极不满,碍於二总管的命令,没人敢找九的麻烦。
但人是经不起挑衅的,九深諳此理,大白天里能不面就不面;当着送饭之人的面,也要装出被工作累成狗的样子,唯一能溜出去放风的时候,也只有在眾人睡下的深夜里。少年非常庆幸越浦有这麼的鬼市,通宵达旦,绝不令人到无聊。
钟阳若要寻晦气,大可派人守着、甚至到哪儿都跟着他,只撂一句“等门到丑时一刻”,九已是万分承情,无意再刺堂堂执敬司三班行走之首,识相地夹着尾巴滚蛋。
兴寧寺外的鬼市不是最热闹,却是越浦极特殊的深夜一景:沿水渠柳岸迤邐摆开的摊贩琳琅满目,绵延数个街航之长,除了常见的燠爆热食、酒水点心,还有诸多卖玉器古玩、字画古书的摊子。
盖因两条街外的明珠航,是越浦有名的高级风月场,是提供通霄饮宴和风雅娱乐的绝佳去处,不像他处秦楼楚馆,常不到亥时便已掩火熄灯拥美销魂去也,此间各大名楼无不备有慧美多才的佳人、緻可口的酒菜,供贵客雅士彻夜连,直至平明。
明珠航不以侍寝為号召的独特生态,使兴寧鬼市的风貌与别处不同。小贩中卖好酒名酒不稀奇,还有专卖各怪酒的,客人兴致一来,便叫盘桓楼内的閒汉上街沽酒,不一会儿工夫,但见酒贩手託两盘,头顶一盘,盘中各置三五隻小碗,或髹漆或瓷,讲究者也不乏金银琉璃,不比楼内所备稍逊;碗中贮盛各酒浆,异香扑鼻。酒贩子神态自若地踅将进来,竟未洒出半滴酒水,绝妙的身手往往引得艺伎们惊呼失笑,讚叹连连。
小贩将酒碗在桌顶一字摆开,宾客开始竞猜酒名、產地等,除赌酒之外,也赌金银、诗文乃至美人香吻,末了贩夫一一揭晓,解说妙语如珠,客人一高兴便多给赏赐,往往比酒资还丰厚,呼之曰“酒博士”。
其餘如字画、古玩等,各种摊子均有神似而形异的玩法。
九囊中银钱有限,既无意、实际上也去不了风月场所,兴寧鬼市最引少年的,其实是棋摊。
他从小就喜欢下棋,但这儿的棋摊除了常见的围棋象棋,从最简单的剪刀棋、井字棋、老牛棋,到别开生面的双陆棋和斗兽棋,随便数都有十来种。摊主摆开几凳棋具,竖起“一局五文”的墨字木片,坐下的人拿五枚铜钱搁边上,两两开始捉对廝杀。
观棋最有趣的地方,就在於赌。
路人不仅能围观,还能往双方奕者的小几边上放钱,同样是一注五文,然后站到押注对象的身后去,摊主从其中拿走一文,分出胜负之后,赌资由胜方均分。
棋摊的摊主不仅要通各种棋类的玩法,还得有过目不忘的本领,谁放了几文钱、押了哪一边,瞥一眼便能记得,结算时分毫不差,经常赢得围观人群的掌声喝采,也是表演的一环。万一撞上了几十人、几百人围观下注的大场面,也会拿出簿册来一一登记,务求清楚明白,绝不糊烂,以免砸了招牌。
九大半个月里夜夜连,起初下得保守,常常还得放水以免引起不必要的注意,但杨柳岸这厢以棋力著称的摊主,差不多都让他宰过了几轮,谁也奈何不了这名少年。
所幸九為人随和有礼,又言语詼谐,最后与各摊都成了忘年之;遇着下得很烂又霸着摊子不走的老赖,摊主们还会用眼神向他求救,让他用快棋狠剃对方几次头,教老赖夹起尾巴做人。
他在杨柳岸做了好一阵无冕王,只输给一个人过,今晚也抱着“能再遇见就好了”的期待,不料拉开几凳坐下的,却是另一名同样白白胖胖的少年公子。
那人生得一张可亲的娃娃脸,方头大耳、面貌清秀,不但爱笑,笑起来还是那种毫无心机的眯眯眼,委实令人讨厌不起来。九忍不住叹了口气。
“又见面了,公子爷。我直接认输了行不?”捏着衣襟微微敞开,以示怀中别无他物。
“玉鐲我没带在身上,公子爷留个地址给我,我明儿专程送回去,当给您赔不是。公子爷大人大量,别与小人计较啦。”那公子见他苦着张脸,不由得哈哈大笑。
“别误会别误会,我是在里头待得无聊,正巧出来看见人,才来与你手谈手谈。输了给你的物事,哪有讨回来的道理?况且我输得心服口服,高兴都来不及,怎会与这位大哥计较?”举起食指勾了勾。身后从人转问摊主道:“下一局非五文不可麼?多给行不?”摊主双手乱摇:“不多不少五文一局。”从人懒与他废话,“喀答!”掏出一隻银锭,重重放落。
那公子怡然道:“不好意思没带铜钱,这便不用找了。”九与他非是初见。
在越浦数十里外的一间野店,这锦衣华服的年轻公子与横疏影一行撞着大雨避,店小容不下两拨人,钟阳等无意退让,与公子身边的女眷发生衝突,公子提议比试决定谁能留下躲雨,最后九巧计得胜,公子输了枚玉鐲给他,却不怎麼心疼似。
横疏影瞧那鐲子一眼,更无二话,命眾人退出野店,让出雨遮。公子的女眷洋洋得意,听他二人的对话,才知那烈如火、说打就打的美貌少妇居然是年轻公子的亲嚷,若非是幼女怀胎,便是那女子有什麼惊人的驻顏妙术,才能有个这般年纪的儿子。
横疏影上山后,某吉光院闯入大批不速之客,说“我家公子包了兴寧寺”,将执敬司眾人逐出,寺中长老夹在中间左右為难,双方照面分外眼红,原来又是那名年轻公子的手下。
“你们当越浦是自家厨房麼?”钟阳冷道:“到哪儿都是一句话让人滚蛋,眼里还有没有王法?”公子的从人们面面相覷,半晌才爆出豪笑。
“不瞒你说,还真是!在这儿我家公子想让谁滚蛋,谁就得——”被年轻公子打断。
“别乱说啊,不是这儿。”他笑得十分朗,没半点心机。
“要再过去一点才是。在越浦我们不能想叫谁滚蛋谁滚蛋,毕竟不是自己家。”衝九一点头,快带人离开吉光院。
不想相隔未久,长孙旭又三度遇上。能在杨柳岸摆棋摊的,哪个不是老江湖?银两虽好,多收短收都是麻烦,那摊主半天都没伸手去拿,年轻公子全看在眼里,拈起银锭,抬眸笑道:“虽说不用找了,太费了也不好。这枚银子,够请整摊人玩一局不?”
“够。”摊主眉眼一动,立时便会过意来,微喜。
“行,那就请所有人玩罢,剩的全押了。”公子笑道:“押我这一侧赢。但不对赌未免没意思,我再出一锭,押另一侧赢;不管各桌的哪一侧,下赢的我另赏一锭,和局双方各五十文钱。”围观的人群中爆出一阵欢呼,手脚快的纷纷抢空位坐下。
这棋摊子不过五六张矮几,顷刻满座,没抢到的心有不甘,竟一股坐到邻摊去,杨柳岸边整排的棋几就这样坐满了人。年轻公子也不在意,让从人一摊一摊掏钱,下棋的、围观的俱都兴致,现场气氛热络,驻足探问之人越来越多。
九瞧着都不有些佩服起来。他初上朱城山时為求自保,把主家给他的金银散了个光,深知花钱也是门艺术,往街心洒钱固能引人,效果却稍纵即逝,银钱空了人自散去,毫无侥倖可期。
年轻公子押注的钱,除非引来巨量投注稀释了比例,否则最终能拿回的比例仍高。严格说来,他真正花出去的只有请客的那枚银锭,以及打赏胜者的部分而已。
除却原本的棋客,真能凭棋力分出胜负者几希,贪小便宜抢位子的未必通棋,遑论双陆等域外传来的博奕游戏,可望以和局作收;和局虽得不到价近千文的银锭厚赏,双方却都能拿到五十文钱,皆大欢喜。
年轻公子看似豪气,细较之下,至多就损失三五枚银锭,在风月场中随便走过一条长廊,赏出的都不止这个数儿。
“其实我很想认识你。”九回过神时,双手已被年轻公子握住,亲热摇晃。
“我啊叫雷恒,爱是永恒、四季如的雷恒!你叫我就行了。兄台怎麼称呼啊?”
“长……长孙旭。”九觉得他热情到都有点让人窒息了,手掌半天都不回来,訥訥一笑。
“朋友喊我‘九’。”“那就叫你九,你喊我啊。那天你摆平我嚷的法子,实在太聪明——”雷恒似极欣赏他的随机应变,话匣一开滔滔难,两眼放光,如与童党并肩回味恶作剧得逞的光荣事蹟,充满歷战老兵的浓情厚谊。
九朋友不多,在朱城山只一个耿照称得上铁,清楚自已与眼前之人没有稔到称兄道弟的程度,然而不可否认,这样热络自然的气氛令人到十分舒服,就与杨柳岸的河风一样。
雷恒本不会下棋,他们这桌还是海外伊沙陀罗国传来的异域斗兽棋,他只对活灵活现的兽形棋子表现出短暂的兴趣,却听不完规则讲解,两人索溜到旁边摊子喝杏仁茶,自是雷恒请客。
“静月楼外杨婆子的杏仁茶是天下第一。”雷恒告诉他。
“我每次来静月楼都為了这一碗,喝完就想回家了。里面真的很无聊。”两人蹲在静月楼的朱门外吹着热气四溢的汤,小口小口啜饮。雷恒说得没错,久心想,这杏仁茶真是天杀的好喝。
雷恒说话詼谐,连夸大之处也不致令人反,能适切勾起听者的兴致,同那神出鬼没的握手奇技一样,绝对是种才能。但说越浦最有名的顶级院之一“很无聊”,这就有些过了。
九也听过“请客不请嫖”的江湖传言,不会让雷恒带他进去开眼界,只是出一脸礼貌的鄙夷,呼嚕呼嚕边茶汤边冷笑:“……因為艺伎不给麼?”忒想你来明珠航干嘛?这连外地人都听不下去啊。
“有钱都能啊,我都腻了。”雷恒一脸无辜地连放爆击,忽压低声音道:“但今晚的特等房不是平常的那种,在拍卖哩!我很讨厌出价……也不是。我不讨厌竞价,我讨厌的是勉强别人,那就不是买卖,而是糟践了,真心不喜欢。”见九一脸懵,收起刀刀絮絮的埋怨口吻,朗笑道:“他们在竞拍处女啦,说是南陵来的上等货,保证血统纯正出身良好,诸国皆有,绝不是什麼村姑之类。”九“噗”的一声喷得路人慌忙跳脚,那人像被了满裤脚的浓也似,又𫫇又怒,面丕变:“小畜生你干什麼!”说着捋起了袖管。
雷恒随手衝他扔了枚宝石戒指,趁七八人扑上抢夺,把九拉到一旁替他拍背,笑道:“别动别动,这种拍卖会要不挑主办方等级,月月都有,连我忒不爱去的人,每季至少也得出席个一两场,做做人情。不过打着南陵诸封国这种主题的倒不多,我瞧了几个成的确很不错,就是哭哭啼啼的让人心里难受——”九咳到连眼鼻都溢出杏仁茶来,久久缓不过气。
雷恒自顾自说了半天,忽恍然之:“你有兴趣又不敢说,原来是怕我请你啊!真是太有意思了。放心放心,‘请客不请嫖’我还是知道的,请嫖鸡鸡小嘛!别担心别担心。”忽见一名龟奴探头出大门,没好气道:“两碗杏仁茶叫半天了,怎还没来!”雷恒把碗里的倒了点给九,拉他起身:“来咧!”龟奴瞧是两个半大不小的孩子,口气益发不耐:“给大爷死进来!”雷恒笑得开心极了:“来咧!”揪着涕泗横的九跟了进去。
在他看来,冒称帮买杏仁茶赚点微薄打赏的童子,可就不算“请嫖”了,不仅没嫖,连进门都没付银两啊!充其量也就是白嫖空嫖,九肯定小不了鸡鸡。
长孙旭万万没想到他的静月楼初体验是涕泗横、手端白汤,混充进来白嫖,这严重违反他奉行至今的“绝不涉险”座右铭,偏偏雷恒抓人手臂快如闪电,还来不及反应,两人已走在金碧辉煌的静月楼中,迴廊九曲千门万户,眨眼间便已找不到回头路。
明珠航彻夜丝竹不断,為免扰人清梦,隔音都做得相当好,包厢分散於一个个独立小院,院内遍植花树,也能有效隔绝声音。
杏仁茶不是特等房的客人叫的,雷恒趁迴廊转弯拉着九一拐,遁入一座深院,门外几名魁梧大汉,个个太阳高高鼓起,一看就知是重金聘的打手,守卫十分森严。
雷恒把杏仁茶连碗往树丛里一扔,重新穿好了绑在间的锦缎大褂,理平縐褶,叹了口气。
“从这儿起就要刷脸啦。桿直些。”领着九大步行去。门前一名年纪更大、服更讲究的龟奴见了他,恭谨行礼道:“雷少爷安好。”倒也未特别逢陪笑。
雷恒微笑:“我知道路,自己走行了。”龟奴点头称是。二少穿过庭院,却进入金碧辉煌的朱阁,而是在鏤花窗外窥视。
阁厅里有座戏台,台前散着十几张桌子,两侧则是隐密极高的槅扇包厢,看不见里头坐的什麼人。二楼是一圈“回”字型边廊,应是雅座,从窗外一样看不真切,只知是酒楼常见配置,不算新鲜。
此际台上却不是戏班子在演大戏,观眾也较寻常酒楼要安静得多,低鸣的丝竹乐音透着股异域风情,一名少女被两位吗吗扶上台来,穿着一望即知的南陵服饰,主持人低沉的磁嗓音介绍她来自恶水国,芳龄十五,乃国中贵族承桑氏的嫡裔云云。
吗吗们扶着少女在台上转了几圈,忽往两侧一拉,少女全身衣物就这麼倏然两分,宛如变戏法般,出一身琥珀的匀肌,紧实的曲线犹带一丝少女独有的娇腴;从鏤花隙眼看不见全脸,几个仓促闪掠的片段间,依稀可见尖頷隆準、星眸朦朧,应是十分标緻。
“……瞧着是下了药。”雷恒低道。
“估计头几个清醒的无不哭哭啼啼,卖相太糟,不过也可能是设计好的。反差萌——你知道,价钱更好。”顿失扶持,眼神濛的赤少女细腿骤软,娇娇地向后仰倒,台下一片低呼声中,娇躯突然凝住,一名浑身黑衣、黑布遮脸,双手戴着黑纱手套之人托住她,鱼皮似的紧身黑衣裹出诱人曲线,竟是女子。宾客的惊呼转成了零星的掌採低笑,嗡嗡一片,气氛突然热络了起来。
吗吗们与黑衣女扶着少女,分在戏台两侧最前端做过展示,又回台子中央。此间不知何时出现一架既像胡牀、又似木马的怪异牀具,看来也是用了漆黑背景的障眼手法。
少女被摆上牀架,主持人作暗掣,将她柔润的大腿分开,阴阜高高抬起,台上烛照显经过心设计,全集中在这浑圆饱满的销魂秘处之上。
“南陵贵族,自称神鸟族后裔,便化成人形,依旧保有神鸟若干徵候,如某些地方……长的不是,而是羽。”台下爆出零星笑声。九望进窗隙,恰见少女阴稀疏,不甚卷曲,果然颇有几分羽模样。
“鸟呢,和拉屎用的是一处。”主持人道:“都成人了,自得有些讲究,不能这般污秽。但毕竟是神鸟族后裔,还是能看出些许端倪,贵客请细品一二。”吗吗们将少女一翻,成了翘的趴姿。
“相信贵客也都听过,南陵人爱玩后庭,男女皆然。今一见,怕是有几分道理。”主持人接话的时机拿捏甚巧,磁酥酥的低沉嗓音而不猥,眾人听了都笑起来,是充满遐思、极力抑制兽欲,勉强维持着衣冠体面的那种笑。随后展开的竞价果然是暗汹涌,此起彼落的价牌教人差点看不过来。
“……是不是很讨厌?”的声音听来意兴阑珊,厌世浓厚。
“那廝说话是很有趣啦,但这就是不折不扣的糟蹋人。让女孩子笑嘻嘻的推销自己不好麼?你情我愿才有意思啊!这样实在是——”见他望进窗隙里怔怔出神,心念一动,击掌笑道:“既然你喜欢那个小姑娘,我把她买下来好了。”
“等、等一下!”长孙旭吓了一跳,双手乱摇:“我不是……我没有……别乱说……”雷恒含笑拍肩。
“明白明白,否认三连嘛!大家都理解的。你也不用怕鸡鸡变小,咱们只买不嫖,纯朋友你看怎样?”似乎说到“朋友”二字心情特别好,倒是此前九所未见。
雷恒可说是含着金汤匙出生,人生里註定不会有“朋友”这种无用的累赘。
身份相若、能门当户对往来的,全是将来方方面面的潜在对手,丰年不杀歹年杀,自不能掉以轻心;身份低的多半怀抱目的而来,更不可不提防。虽与谁都能说说笑笑,看似没什麼架子,但雷恒天生便有分辨出谁“别有用心”的能力,此既是屏障,也是隔绝。
这名叫长孙旭的少年,不但跟他一样白白胖胖瞧着亲切,人又聪明绝顶,情宽和,还对他无所求。连故意把“芙蓉玉双全”输给他,九瞧着宝物的眼神还不如瞧鸡腿热切,令雷恒莫名生出结的强烈渴望。
况且三次偶遇真不是套路,雷恒并不特别相信缘分,但缘分来时,也没有硬拒於门外的理由罢?
送礼须於点子上。这是他的新朋友少数兴趣的玩意,连下棋九都没这般眼直。雷恒下定决心,要為他拍下这头可人的小小雀儿。
长孙旭直到这会儿,才知“命薄如纸”四字,不是什麼艺术渲染,而是某人、某时或某段的坎坷人生,血泪斑斑,从来就不容易。
当年母亲怀着他逃出南陵的事,其实母亲甚少提起,九隻知梗概,对他来说是没有画面的。但透过朱阁中戏台上赤的无助少女,这恐怕是少年首次鲜活地体会到那段他虽有参与、实际上无有记忆,遑论同苦的千里亡命,是多麼可怕又令人哀伤的经歷,难以自制地思念起早逝的母亲来。
要不是打断了他的怀缅和悼念,九说不定会久违地掉下眼泪。
“当个朋友嘛!你想想……”雷恒继续发挥商人之子的口舌才具,循循善诱:“等你成了她的男朋友,再就不算嫖了啊!不用怕鸡鸡小了不是?”这理论一听就极不对劲,但九竟无法反驳。有钱人的想法我们果然是不明白啊!
雷恒心想这也该说服他了吧,兴致道:“是吧?包在我身上!等我好消息啊。”一溜烟窜进阁里。不一会儿工夫,场内响起低呜呜的连片惊呼,想是雷恒雷少爷出手了,举牌竞价的无声廝杀顿时陷入一片惨烈血海。
九试图穿越门,想也知是徒劳,况且他也不晓得人在哪个包厢,来不及细瞧就被撵出了厅门。
少年赶在龟奴唤人前避入阁廊檐影,五绕三拐地摸到后进,找到一扇未上锁的门户潜入。阁内一如外头的园景般曲折,他凭步幅计算廊廡短长,与屋型、大厅格局相对照,在脑内迅速画出平面图,寻至戏台后方一处堆满物什的广间里。
喊价的声音从出场门传来,可想见外头竞价之热,后台却意外的没什麼人。
一名个头异常娇小的少女,托腮坐在下场门后头,隔着垂帘望齣戏台,背影窈窕浮凸自不待言,更隐透着一股难以形容的强大气场,周遭杂物掩不去玲瓏娇躯,如锥处囊中,其末立见。
少女非是肌肤,雪颈柔荑都白到了极处,可说是长孙旭平生仅见的白皙。他知南陵女子不全是小麦肌,诸国族繁苗眾,各有不同,他母亲就白如羊脂玉似,说不定主家最初就是被这点给上了。
踅到少女身畔,还未开口,她便径向一旁挪出半个身位,长孙旭遂与她并肩坐於偌大的衣箱盖顶。
少女幽香细细,透出温热的颈领间,嗅得人心猿意马,却不是胭脂水粉之类的人工气息。他怕被当成登徒子没敢转头,餘光依稀瞥见浓睫弯似排扇,琼鼻尖尖、桃腮透红,翘显眼的下巴得极具个,不用多看亦知是美人儿,否则也不会被拐卖了。
“要不趁没人看守……”开声之际,长孙旭才发现喉咙嘶哑,还有些破音,陌生到完全不像平时的他。而吐出的字句,则令他五倍……不,该有十倍的诧异加懊悔,恨不得毒哑自己。我他妈是中了什麼用蠢话狠搭汕的?
“我带你逃出去?我可以说你是我妹妹。”来吧,鄙视我吧,用你可爱的脸蛋做出最不屑的表情,把我当成会说话的蛆就好,这是说了蠢话狠应得的下场。
“我带你逃出去”是什麼鬼?妹妹什麼的更是尬得飞起……你怎麼不乾脆问她“海你知道钢材有几种”、“热锻和冷锻哪里不一样”、“敷土成分你怎麼看”算了?
再怎麼於心不忍,九也没有凭一己之力拯救这些少女的念头,甚至不觉得买下她们称得上是拯救。贩卖人口是结构极庞大、牵涉极复杂的现象,不彻底改造国家,本不可能绝,其难度不亚於改革土地,重新分配资源等,不是他这种人该想的事。
况且这些少女若真从南陵被劫来,于越浦举目无亲,落街头的下场,可能比被富商买回去当玩物更惨。
少女用都都的翘下巴往后一比——自是背向他,九再度完美错过她的正脸——道:“后头两排房间里,起码还有二十来个,娘有生这麼多妹妹麼?”声音似乎带着笑,觉俏皮的,居然接了他的蠢话狠。
长孙旭咧着嘴傻笑起来。
原来天……是这种觉啊!呵呵。
活在这世上真是太好了。
他知输给自己的玉鐲价值连城,莫说买下两名南陵处女,能买半座静月楼他也不意外,长孙旭一直想找机会归还。此际却不由得踌躇起来:乾脆拿鐲子同换她俩,还能多要一笔送二殊返乡的盘缠和安家费——“杀光好了。”少女托腮喃喃道。
“……什麼?”长孙旭闻言转头,忽说不出话来,彷彿被正面一拳打塌口,不进半点空气。
这是他这辈子见过最漂亮的脸蛋之一。
母亲很美,二总管更是人间绝,但比起眼前完美合了艳丽与清纯、娇柔与颯烈,连狠厉眥眸都灿若晓星的少女,母亲和横疏影显得太软糯,美貌便甚,也不似这般冷冽割人,痛处又带着热辣辣的颯利快。
“萝哩萝唆的啥事都别干了。”少女娇笑着,媚人的眼神倏凛如刀,既老练又天真,很难判断哪一面才真是她。
“在杀你之前,先让我料理这帮子王八蛋,瞧着心烦。你别跑啊,乖乖等我,不会太久的。”